索南才让,蒙古族,青年小说家。一九八五年出生于青海。作品发表在《收获》《十月》《花城》《作品》《民族文学》《青年作家》《红豆》等杂志,作品入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中华文学选刊》等选刊以及收获文学榜、《2020青春文学》、《2021中国短篇小说20家》、《2021中国微型小说年选》等年度选本和排行榜。曾获《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佳作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青稞文学奖、红豆文学奖、青海省青年文学奖等奖项以及青海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等。二〇二二年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代表作为《荒原上》《巡山队》。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1
春末,我从失去亲人的旋涡中摆脱出来,心境平和下来。我开始习惯一个人生活,有了很多无所事事的空荡荡的时间。为了不过于浪费这些宝贵的光阴,我比以往更用心地关注牲畜的身体状况,一有不对劲便未雨绸缪,抢在病情严重前治好。为此我需要多方面去分析研究,要做很多功课。但好在只要用心,这事并不很难。十来次以后,我已算得上兽医方面的专家了,很多疑难杂症我都可以试上一试,不至于手足无措。我这才发现牲畜有那么多疾病,这些疾病一天天严重,只等最适合的时候暴发出来。一想到过去有那么多牛羊因为我的照顾不周而在病痛中默默死去,我就有些惴惴不安。假使我不曾遭遇这次痛苦的失亲灾祸,我又何尝注意到这些呢?他们遭遇车祸以后,我常常想起那些被马摔掉的人,他们在骑马行进中殁了,让人感觉遭遇车祸一样。
叔叔从青海湖上端的草原顺着牧道,骑马来看我。他已经五十七岁了,大脑袋上是针一样密密麻麻的灰白短发。他的身材依然那么瘦。这一辈子他都在羡慕身体肥胖的人。他下马时很艰难,我快步跑过去扶住他,我们拥抱了一下。叔叔拍拍我的肩膀,乐呵呵地炫耀说,来的路上碰到一个老妇在伸胳膊伸腿锻炼身体,他们聊得很过瘾。她家屋舍畜棚连成片,是大户人家。
那天晚上,我戴上他送给我的手表。这表是他去年到云南旅游时买的,一块银表链黑表盘的杂牌机械表。
“我一直观察你,你没有手表,而且你也没有好马,这可不行,你都三十多岁了。”叔叔说,“兰台吉,你再不好好过一把年轻的瘾就老了。”他说明来意,想让我去帮他剪羊毛。
叔叔问我:“你的羊毛剪完了吗?”“我今年雇人剪的。”我说。叔叔问:“剪一只多少钱?”我说:“三块五。”叔叔又问:“这么贵了吗?”我告诉他:“去年还是两块八,后来涨到三块。”
雇人剪羊毛的牧户太多,剪羊毛的人趁机涨价了,不过还是剪不完,羊太多了。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一些传统的做法遭到拒绝了,因为现在没有人会笑话你做事,只要你自己愿意就好。所以尽管卖羊毛赚的钱都不足以支付剪羊毛的开支,但谁都想图个省心省力。[page]
第二天,我们俩吃了早饭,叔叔在我的羊圈里检查羊群。他总算对我有了一点满意,说我的羊还能看。他尤其对我挑选留下的十五只公羊羔和十五只母羊羔赞赏有加,说都是好羊羔。我们将羊群放出来,等它们喝完水,朝草山里走去,我们跟在后面。因为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叔叔右腿瘸得有点厉害,上坡下坡都很吃力,可他的兴致很高,对羊评头论足,卖弄他的经验。从草山回来,我们骑着摩托车去赶马。既然叔叔坚持要我骑马,我就得先套住我的马。我已经想好了,走远路就骑那匹鞍口软和的银鬃骟马。它有点老了,但还足以应付几十公里的路途。我有一年多没有接触它了,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少。在它还是一匹青壮马的时候,它最害怕的是红颜色的东西。如果我骑着它在路上走,遇见了红颜色的东西,它就会发飙。它对红颜色的恐怖传染给了我,以至于我看见红颜色的东西也不受控制地生出恐惧感,我总觉得看见了红颜色的东西我就要倒霉了。
到了另一个草场的门口,我让叔叔下车,在门口等。他手里拿着一条长长的尼龙绳,等会儿马群来了拿来套住银鬃。他的神态略显疲惫。昨晚吃过晚饭后,我们喝了一瓶白酒。我喝了二两不想喝了,说:“喝酒的次数越少酒量越差。”叔叔对此话嗤之以鼻,他面不改色地说:“没酒量就是没酒量,找什么借口?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更差劲了。”我被说得面红耳赤。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谈及去世的亲人们。我的银鬃又惹得叔叔啧啧称奇,说我把马养出了猪的肥膘,实在难得。“我一年多没有骑它了。”我说。“那你养着它干吗?这就是白破脸的儿子?”“对。就是小时候不会过围栏的那个小银鬃,您有八九年没见过了吧?我骑过那匹老母马,现在连它的孩子也老了。”叔叔感叹:“那时候白破脸很年轻,走路那叫一个稳当。”
白破脸早已化作一捧尘土,与它同时代的一批良驹的光辉也只存留在一些老人心中,成为一丝半点的怀念。我们将马群堵在围栏的角落里。叔叔总有先见之明,知道哪一匹马想冲出去,并事先堵住它。他套马只用了三分钟不到的时间,一边在手中盘绳子一边观察银鬃的移动方向,计算将绳子甩出去后银鬃的反应。他把这一切考虑好了绳子也在手中形成了最完美的盘圈,他一刻也没有停留便将套绳挥舞出去,直奔银鬃头顶。而银鬃被套过多少回了,心早就有戒备,绳子一甩上天空它就跑动起来。叔叔之前一直都没有看它,就因为怕它发现自己就是目标,但绳子一甩上天空它还是紧张地跑起来了。但它的经验和智慧显然是不够的,它好像是自己眼巴巴地跑进了套绳,它反应过来时已经被套得牢牢的了。银鬃也很聪明,发现事已不可挽回便死了心,乖乖地站在原地等我走过去套上马笼头。它迅速调整了心态,对我摆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我把缰绳递给叔叔,接过套绳。那匹黑灰在流鼻涕,我得看看是怎么回事。“不要晃动绳子,藏到身后去,等找到时机马上甩出去。”叔叔说,“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不服气地犟了一嘴。“那你的胳膊那么僵硬干什么?”他厉声呵斥,“你老了吗?”他一发火,我再怎么不服也得乖乖闭嘴。我拿出最大的本事把套马技术给他表演了一次,很成功。他的怒气消了些。黑灰激烈地挣扎时他看着,等我将它的三条腿扣上马绊后他走过来,一把揪住黑灰的耳朵,另一只手扳开它的嘴,朝嘴里观察了一会儿。其间黑灰两次挣脱,它高高地仰着头不让叔叔再碰,但叔叔办法多的是,它坚持不了多久便乖乖就范。叔叔说:“没事,小小的感冒,很快会自愈。”[page]
回去的路上,我骑着摩托车,叔叔坐在后面,牵着银鬃的缰绳。它很近地贴着摩托车跑。叔叔观察它跑步的姿势,说它年轻时一定是经常踩到自己的前蹄腕子。然后他评判草场的优劣。他很客观地说我去年放牧超载,导致今年草场长势堪忧,如果雨水不够的话,届时什么也不会留下,到那时我就和羊一起去喝西北风了。他简直有点幸灾乐祸,做了一个OK的手势。我被他逗笑了。他身上有那种牧民一辈子和牲口打交道而形成的带着青草味、羊膻味、马汗味和他自己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属于他们那一代牧民特有的气味。这种气味太独特,就算我没有眼睛,我也能轻轻松松地辨认出他们。
我们出发时已是上午十点多了。从家里到铁路涵洞这段路上,他谈话的兴致很高。“想当年我一次能喝三瓶白酒,就算喝了第四瓶,也能把缰绳牢牢握在手中。你听说过我喝醉了被马摔下来吗?”我摇摇头。“那你被摔过吗?”他接着问。“我很少喝酒的,叔叔。而且更不会有喝醉了骑马的事情。”我说。“那你要小心了,你清醒的时候被摔,不但不好而且没意思。”他话音刚落,我已经控制不住突然受惊的银鬃了,被摔在地上。身体并无大碍,只是看着叔叔奸计得逞的样子感到很郁闷。他明明看见了那块塑料,却没有提醒我,不但不提醒我,还故意挡住了塑料不让我早一点看见。
下午四点,我们到了叔叔家。
2
叔叔摘下两匹马的嚼环,把马牵到屋边的草地里。马鞍需要等马身上汗水干透了才能卸掉,不然马容易感冒。叔叔心疼马,照顾得细致,断不让它们多受一份罪。
他家的拴马柱离家有两百米远,因为婶婶不希望在家里闻到马粪味道。她对马粪严重过敏,而且几十年极少去碰马,她不管是什么季节从不摘掉口罩,很认真严格地保护自己的鼻子,从而有了另一方面的显著效果,她的面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上十几岁。
婶婶从窗户里看见了我,在向我招手。毫无例外,她这次也穿着这十年来始终固定的装束——一件蓝花的女士西服,一条紫灰色的条纹裤子,一双黑色的方根皮鞋——仿佛从十年前开始她就定格在此了。但我还是发现了一丝不同,她手腕子上戴着个明晃晃金灿灿的手镯。她正在用这只手跟我打招呼。她指指手镯,嘴里说着什么,脸上笑容灿烂。她出现在门口,埋怨我一年到头都不知道多来看看她。
“好漂亮的手镯呀,是黄金的吧,谁给您买的?”她高兴地把手臂伸给我,让我好好看看。“你叔叔买的,说是我们结婚三十年的礼物。”“哎呀呀,叔叔这么浪漫,还知道送结婚纪念日礼物。”我感到诧异极了,就我所知,他送给我的表还是婶婶的意思,表也是婶婶买的,就叔叔那德行……[page]
婶婶白了我一眼,问:“什么是银婚呀?我问是啥意思他又不说。”“结婚三十年就是银婚,五十年是金婚。”我说。“哦,是这样子啊。”婶婶若有所思,“那应该买银子,银婚不是银子吗?“那不行,档次太低了,银婚戴金,金婚配钻才对嘛。”“钻石?”婶婶一个劲地摇头,“那我可不要,现在戴这个镯子我都觉得太不好意思了。”“怎么会?您和十年前一模一样,甚至好像更年轻了。”我说。“你这张嘴,和你弟弟一样能说。”说到她儿子,婶婶的情绪低沉下去了。
婶婶的儿子,我唯一的堂弟,已经很久没有音讯了。但我们知道,在某一天他会像以往那样突然出现在家里,睡在沙发上,让老两口大吃一惊。而他会表现出像是去镇上买东西回来了,又像是放牧回来了一样。有时候他会带来一个女人,说是老两口的儿媳妇。但他带回来的女人不是媳妇只是对象,让老两口看看合不合适。而更多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回来,接过老父亲手里的马缰绳,笑容满面地对待父亲。他去羊群,去牛群,他需要把一些合适的牛羊兑换成一些更有用的纸片来压住郁热的心口。
而叔叔呢,从来没有对儿子发过火生过气,好像他辛辛苦苦将牛羊放牧好,儿子回来卖掉换钱去花让他很荣幸。叔叔神经病一样将儿子宠到天上去了,但叔叔会抱怨儿子说,这都多少岁了,连媳妇都找不到,害得他连孙子都没有。而这样的话自从去年开始他再也不说了,因为堂弟带回来一个孩子,一个几个月大的男婴。叔叔和婶婶只看了孩子一眼,就确定无疑孩子是他们的孙子,因为和堂弟小时候长得太像了。老两口出乎意料地得到一个宝贝孙子,这个意外让叔叔产生怀疑,他审问堂弟,是不是还有他的孙子孙女遗留在外,是不是已经在外面有了好几个孩子。我这个堂弟,好像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说:“老爸,你是不是觉得你儿子是个傻瓜?我会做那样的蠢事吗?那怎么可能呢?”叔叔生气地说:“这怎么就是蠢事了?是我们家的骨肉。”堂弟十分严肃地看着叔叔说:“老爸,不是所有女人都有资格给你生孙子的。”他认真严肃的劲儿把叔叔唬得一愣一愣的。
堂弟的儿子长得像羊羔一样快。叔叔和婶婶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捆绑在孙子身上,孙子的哭喊声驱赶掉他们的烦恼和疲劳。自从孙子来了以后,婶婶变得更麻利更有精神了,她每天要在孙子的脸蛋和小嘴巴、小手、脖子、小脑袋、耳朵、小屁股等地方亲几十次。老两口和名叫达瓦的孙子相依为命。这么说好像不太合适,事实上是他们更有干劲和目标了。这从家中里里外外的变化和他们身上的气息变化中能看得出来,他们简直是青春焕发。[page]
婶婶走在前面,笨重的身体增强了生命的力量,她仿佛是在将生命拿捏在脚下,她的整个人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厚实了。
小达瓦在那张巨大到夸张的大炕上独自玩耍,听见声音他抬起头,看见婶婶便笑起来,爬过来。我从婶婶怀里接过小家伙,但他很抗拒我抱着他,开始哭泣。婶婶立刻伸手抱回去,小声念念叨叨地安慰,但他就是不安静。叔叔进屋来,小家伙又要到叔叔那里去。我仔细端详了这个侄儿的模样,的确有堂弟的影子,而他调皮的样子就更像了。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了另一个靠不住的野小子在飞快而野蛮地成长起来,准备接着吸食这对老人的血肉。
3
这天晚上,老两口和爱孙吃饱喝足,在大炕上嬉闹累了,他们酣然入睡。我睡在另一个房间。半夜里我被叔叔摇醒,忘了身在何处,心想叔叔怎么来了。“快跟我去赶羊,”叔叔小声说,“下大雨了。”
睡觉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天上黑乎乎一片,一颗星星也没有。我提醒叔叔把羊群关到棚舍里,别让羊毛湿了耽误剪。“天这么热干吗把羊关在棚里受罪?再说了,天也不会下雨。”他笃定地说。婶婶辩驳了一句,他说:“我心里有数。”我们就没再坚持。但雨是真的来了。我套上衣服走出去。外面风很大,雨水齐刷刷地朝着一个方向倾斜而下。屋上的雨水从六个漏水槽冲下来,形成一面雨帘,砸在红砖地上响成一片。借着外屋的灯光,能看清密集四溅的水珠中蕴含的不同的光彩。叔叔已经在羊圈里了,吆喝羊群往棚里去。但有时候,就是那些关键的时候,不如意的事情会发生。面对黑洞洞的羊棚门口,面对它们已经很熟悉但如今却看不见里面有任何熟悉身影的羊棚时,它们的恐惧出来了。它们不冷,它们被大雨中突然出现的主人和接下来的未知给吓住了,于是没有一只羊带头走进黑暗的棚舍中。往日里英勇的领头羊,这会儿胆怯得被鬼附身似的,连一般的母羊都不如。叔叔气得火冒三丈,站在粪水泥泞的羊圈里破口大骂,将羊的祖宗都骂了个遍。他声音冷酷,行动迅捷。我走进羊圈,他冷冷地瞅了我一眼。在我们两个人的合力围攻之下,终于有一只羊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它非常谨慎地探着头,用心观察。这是一个绝佳时机,我和叔叔不用通气,几乎同时呼喊大叫起来,朝羊群猛地扑了一下。羊群受惊往前挤,那只羊和跟随其后的几只羊挤进了棚舍。而后便轻松了,羊们争先恐后地闯了进去,咩咩一片嚷叫。
“是那一只每年都生双胞胎的黑眼圈母羊。你记得吧?那个大犄角母羊。还是年岁大了的靠得住。”叔叔说,“还有那只大公羊,蛋蛋很大的那只,你记得吧?”我当然记得那只母羊,它肯定很老了,很多年前,它年年都生双胞胎,而且还能毫无意外地将羊羔带大,真是好母羊。而那头种羊就更有意思了,它身板高大,肌肉、犄角发达,毛色纯正,是百里挑一的顶级种羊。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那惊人的硕大的阴囊。我记得我前年将它借去给我的母羊配种。一个夏天结束,转场的途中,我从头到尾看着它走在我前面,甩动它那巨蛋艰难地走着。巨蛋摔打在大腿外侧,走得越快摔打得越频繁。我都看得蛋疼,几乎难以忍受。而它当然更不好受,路途的后半段它几乎是缩背弓腰才坚持下来的。我生出恻隐之心,哪怕给别的牧民让出牧道也不愿意再让羊群疾速前行。有六七次我堵截在羊群前面,让羊群停下来,让它喘口气,让它歇歇那可怕的累赘。冬至那天,我将它装进借来的微型小货车,送回叔叔家。[page]
它还是那样吗?我一想到它的状况就感到难过。
不知道是不是老了,它的那对家伙越来越大了,那皮袋子越来越松垮了……也越来越长,快要拖到地上了。
我能想象那种场景,感到一阵揪心。“太可怜了。”我说。“可怜?”叔叔乐起来,“我看没有,它可不老实,一直厉害得很哪。”“那肯定的,一看那家伙就知道了。”我们心照不宣地哈哈笑起来,任雨水浇湿身子。我们好像很享受这种遭罪的感觉,站在臭烘烘的羊圈里不肯离去。我想起因为这只种羊而遭受到的那些嘲笑,以及由此得到的名声,至今感到尴尬。“它可把我害惨了。”我说。“怎么啦?”叔叔不满地看着我说,“你还不念好?”“现在我们那里的人都叫我甩蛋蛋了。”我说。“哦,那肯定是你不老实。”他将手电照在我脸上,很肯定地说。“它的几个后代我都留成种羊了。”我说,“现在看着挺正常,不会像它那样子。”“我见了,除了那只直角,其他的不适合留到成年。”叔叔说,“而且你的一些母羊也不咋的。”“能生出好羊羔就行,而且我很快会更换的。”我说。“你还是没有用上心思。”叔叔说,“剪完羊毛,我给你找个女人。”他兀自嘿嘿一笑。我们回去,将惨不忍睹的鞋子脱了扔在外面,用廊檐水洗净了脚。大雨一点没有收敛的意思。
4
第二天早上,雨虽然小了些,但仍不适合剪羊毛。叔叔有些不甘心,但也没有办法。他叫的说好来帮忙的几个人都打来电话确认情况,叔叔说推迟至明天。但还有一个人是婶婶亲自打电话过去的,叔叔对我说:“你去接一下,这个人必须要来。”婶婶给我说了线路和那个人家的房子特征。
“本来我是想让你堂弟和她处对象的,但是你看看你堂弟,心思不在家里。”婶婶一副黯然神伤的样子。她这副样子在叔叔面前肯定是不敢出现的,就算在我面前,婶婶也很快收拾好了心情,转而露出愧疚的意思。她说:“那女娃叫桑吉,是一个很好的丫头。我们不能害人家,我和你叔叔就跟她说,你们先见见面,你好好看看人家,你会满意的。你的踏实可靠我跟她做过保证,但她因为你堂弟的样子还是有点怀疑你,你去把她接来……好好看看……”
我穿上雨衣,朝叔叔不怎么开的那辆夏利车跑去。这辆破车很难启动,好一会儿才动了起来。这辆车是堂弟开来的,应该是三四年前吧。他用了一个星期时间教叔叔学会了驾驶。但叔叔更喜欢骑在马上,他不喜欢开车。
在泥浆横流的道路上,车轮半是滚动半是滑溜,行驶得很别扭。半个小时走了不到三公里。雨势渐渐磅礴,四野声势大起,一片灰蒙,根本看不清前面的状况。因为路被雨水灌成了河道,而两边的草地却高出路面,于是车子就像是在窄河上行驶的小船一样起伏。我终于找了个合适的坡度,将车开到草地上,我怕再不出来就会陷到水里面。[page]
草地上一撮撮蒿草圈形成了障碍,车走得更慢了。雨刷器疲软无力地左右刮摆,湿气从四面八方钻进来,挡风玻璃被湿气遮盖,我好像被闷在了一个湿漉漉的玻璃瓶子里。我在储物箱里找到了一块红抹布,一遍又一遍地擦去玻璃上的雾气。汽车蠕行了将近四十分钟。我出发前,婶婶简明扼要地说:“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会看见紧挨在路边的一栋房子。经过这栋房子到下一家,一栋有红色的铁皮屋顶的房子就是她家。”我应该走了七八公里,看见了几栋房子,但没有看见紧挨路边的那栋。有两次我不得不停下车,到外面去查看。前方灰乎乎的,没有房屋,没有树木,没有人影,也没有牛羊。这片撑开的原野上,只有雨水从天而降的声音。
再行驶二十来分钟,终于看见了那栋房子。再往前不久,红铁皮屋顶也出现了,想必这就是她家。有一条更小的路通向她家。但这条小路也已经成了一条小河,根本不能行车。我停好车,冒雨朝那边走去。怀着一种糟糕的心情,我终于站在房门前,雨线中有人打开了门。这个女人很年轻,有一张很整洁端正的脸。如果我的眼神没有问题,她应该是结过婚,甚至生过孩子的女人。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到这些。我的打算是应付应付婶婶,免得她伤心。我说明来意后对她说:“桑吉,我们赶紧走吧。”桑吉转身关好门,我们一起踏进雨雾中。雨声变幻莫测,有一股接一股海水浪潮的声音。我看她的背影,身材削瘦,不说妙曼多姿,却也苗条。
我们坐上车,都不自觉地松了口气。“这雨太大了,应该好几年没有这么大的雨了吧?”我尴尬地说了一句。“你们那边大概要起洪水了。”她看向窗外,答非所问地说。“我们那边?大沟吗?”我惊讶地看向她。她说:“天气预报说青海湖大暴雨。”“是吗?你确定吗?”我听她这话,担忧涌上心头,我虽然将家里的牲畜都交给了好友照看,但如果发洪水的话就太危险了。我想我得尽快回去。我一边开车一边腾出手来擦玻璃。她好像想帮忙但又没开口。过了一会儿,她摇下车窗,让我停车。还没等车停好她已经跳下去,在草丛中拾起半截竹竿。她回到车上取过那块布,缠在竹竿一头。她试了试,刚好可以从副驾驶擦到我前面的挡风玻璃。她说:“走吧。”每隔一会儿,她都伸出竹竿,在车窗上下滑擦几下。多一个人在车里,车内的湿气加重了,她身上散发的热气味道很怪,初闻时有羊粪的气味,但那只是一瞬间的微弱气味,而后是长久持续的洗发水和护肤品的淡淡香气。我发现她的指甲剪得干干净净的,没有涂抹指甲油。
回去时更艰难。我还是没有走那蔚为壮观的“水路”。但在复杂的草地里绕行,困难每一分钟都在增加。我不停地停车下车探路,走得越来越慢。她自告奋勇说要帮我去探路,并说她也会开车,知道分寸。我将雨衣脱给她穿上。再一次停车后,她下去探查前面的水坑,回来时很有经验地说:“没问题,可以冲过去。”她变得豪迈起来,不停地擦去脸上的雨水。她的头发里蓄积了大量的雨水,水不停地流到脸上。我好奇地问:“你怎么那么熟悉大沟呢?”她说:“我在那里住过。”我问:“你在那里有亲戚?”她说:“我姐姐在那里。我姐叫恩措。”我恍然大悟:“原来你是吉保的小姨子啊!怪不得我看你有点面熟呢,原来是恩措的妹妹。吉保从来没有说过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姨子……”[page]
“你认识姐夫?”“我何止认识,我简直……也不对,我要是十分熟悉的话那应该早就认识你了,但我们真的很熟悉啊,那个混蛋居然如此防范我。”她笑了笑。我心里明白她笑什么,所以我也笑起来。车中气氛随之一变,我们都觉察到了一种淡淡的喜悦。她第一次表现出扭捏的样子。我虽然盯着前方的路,但心思却在她身上。“如果早认识几年,说不定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或者有更好的关系了。”她装作没有听出话里的意思,但过了几秒钟,还是小声说:“现在不是认识了吗?”我说:“是啊,缘分是挡不住的,哪怕是吉保也不行。”她斜觑我一眼说:“别欺负姐夫。”我做了个鬼脸。她小拳头砸过来,说:“你这是什么表情?”我说:“我要狠狠地说吉保的坏话,因为我吃醋了。”她说:“你吃哪门子醋啊?你这人真奇怪。”我说:“我也这样问自己啊,然后我就告诉自己,你也太厉害了,喜欢上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她一愣说:“姑娘?哈哈,你笑死我了,我的孩子都成姑娘了。”我说:“那你应该知道一句话。”她有些警觉地看着我。我说:“有句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她哼了一声:“我可没看出来。”我问:“没看出来什么?”她说:“我没看出来我在你眼里是那样的,你在看我笑话吧?”她又表现出一副怀疑的样子。我问:“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我感到很奇怪。”她说:“因为你刚才见到我的时候,我可没看出来你有这个意思。”我脸上有些发热,说:“对不起啊,刚才我确实不够礼貌。”她说:“你婶婶说了吗?”“对呀,然后我才来的。”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怕不合适。”她说:“你问吧,我没那么小气。”“我堂弟是什么样的人你肯定知道,但你为什么又愿意和他处对象呢?”她接过话头说:“谁说我要和他处对象了?”
什么意思?我看着她羞恼的神情,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一个可能,但我实在不敢相信。
她扭过头看外面。“哎呀,哎呀,这个婶婶,她怎么能这样?她这不是截胡嘛?太过分了……不过,不过你也别生气,原谅她的胡闹,她也挺可怜的,你看,最终我们还是见面了。”我安慰她,这才明白婶婶那种愧疚的表情是什么意思。她说:“你都不知道你婶婶有多么执着,她非要我和她儿子交往一段时间,还说所有人都误会了她儿子。”我问:“那你是怎么让她改变心意的?”她笑笑说:“很简单啊,我说只要她儿子不再出去流浪我就考虑考虑。这招真高明,一击即中。”我朝她竖起大拇指,说:“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我的意思是你肯定是很了解我才有了这个想法的,你是从哪儿了解到的?你姐姐吗?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可能吗?”她大大方方地承认了。“哎哎,这个婶婶,害得我留给你不好的印象,真是冤枉。我跟你商量个事。”“什么事?”这会儿她侧过身子,很认真地凝视我。我说:“你能把之前那些事情从你脑子里删掉吗?就当我们是现在才认识的。”“已经晚了。”她佯装伤心的样子,说:“我现在在想,我是不是太主动了。我以为我们都已经结过婚,就不必像第一次那样麻烦了。”我说:“是的,没错。可是我太冤枉了,我都不知情。到现在我都很惊讶,一方面我还有很多疑问想要问你,另一面你在万千人中选中我,让我感动又骄傲。我在想这份沉甸甸的情分,我该如何去呵护。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都乐开花了。”[page]
这个早上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我可以预料到的。婶婶的心思、叔叔的心思、她的心思……我有一些不适应,但我对桑吉已心生爱慕,她让我受宠若惊,我居然会被如此看重。虽然我不了解她,但我相信婶婶,她要给晚辈找的媳妇,绝对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看样子她似乎已经想通了,把我叫来就说明了她的意思。我想我已经大致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套用一句老掉牙的话就是好人有好报。
5
桑吉入神地望着朦胧的天际,开口说自己的往事。
“我有一个女儿,今年十岁,叫英格玛。”“一听名字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我说。“她调皮得很,小嘴会说得不得了,我常常被她气哭。”“哈哈,我都迫不及待想要见见英格玛了。”我说。
她离婚五年了。前夫和一个中年妇女的那点破事被她发现后,她二话不说就离了婚。起先那个混蛋还想玩玩手段,但她又不是吃素的,哪能让他得逞?三下五除二便将事情处理掉了。离婚后她终于放下了心事,有了活力。
“我那时候无论怎么做都没办法让自己乐观一点,我那时候对英格玛很凶,但她好像不在乎,或者她那么小就已经懂事了,宽容地理解我。就算没有那个女人,我也会离婚的,因为我绝不和打老婆的酒鬼一起生活。”她缓缓地说着,脸上是一种很后怕的表情。她好几次捏紧了拳头,在给自己鼓劲。我也握紧了方向盘,这种后怕、这种恐惧,我也不是一直在承受吗?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坦然面对这个悲剧?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因为我不可能想起父母的惨状而无动于衷。我看着她的脸,亲近感油然而生。
她说她和这个男人结婚几年,却很少见到他。最长的一次他消失了七个月。她说:“我不想英格玛在这种环境里长大,趁她还小,我带着她离开了。”我说:“真是瞌睡了送来枕头啊。”“什么?哦,你说的也对。没错,就是按照我的心意来了,但这也不能算是我的错。”她说。我说:“当然不能,你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我很肯定地说,“而且在我看来,你对那个男人还是太优待了,你给了他太多机会。”她说:“那也是应该的,不管怎么样那时候我们还是夫妻。不过事情早已过去了,最终我赢了,但也彻彻底底地输了。”
她甚至没要女儿的赡养费,没要一分钱的财产——哪怕那些财产都是她辛辛苦苦挣出来的——就是因为她怕被纠缠,她需要没有任何纠葛的切断。她带着女儿净身出户,但一点不害怕。因为她还有依靠,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她在娘家那边还有份子——一些牛和羊,一匹马,还有虽然不大但很好的草场。这些“嫁妆”早在她结婚的第一年她的父母就准备好了,他们在每一只羊的脊背涂上和家里不一样的颜料作为记号,从此分别开来,这些羊就是她的。他们在每一头牛耳朵上打上不一样的耳穗……所有的都准备好了,只等一个吉祥的日子,他们将女儿女婿请来,做一桌好菜,正正规规地将这些“嫁妆”交到女儿女婿手上。但事情还没有做就被她阻止了。老两口立刻意识到了什么,却什么也没问。此后她的“嫁妆”就寄存在娘家,母牛生下的牛犊一头也没有卖,她的母羊产下的羊羔,父亲挑最好的二十只留下,其他的卖了,将钱存进她的银行卡。每年的牲畜生产完了,父亲会给她打电话,或者她回娘家时,父亲给她汇报一年的收成和损失:因为什么原因死了几只羊,又出生了多少,卖掉了多少……[page]
每次她先是发脾气,气她父亲说这些,而后开始哭。其实她的心里别提有多幸福了。后来她离婚了回到家,将三岁多的英格玛往父亲怀里一放,老两口比她结婚的时候还高兴。她以为接下来会是一番介绍、相亲这种让人颓气的日子,奇怪的是整整一年他们没有任何动作,好像她结过一次婚就再没有婚姻了。最终是她压不住内心的好奇,问了母亲。母亲对她说:“我们再也不掺和你的感情了,说来说去还是自己找的好。你怎么不去找一个?”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第一次相亲,无论如何我都很感激你婶婶。”她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就没我什么事吗?”我夸张地嚷道,“我是你的对象,怎么就没我什么事了?”她说:“你胡喊什么?”我说:“能不喊吗?我全程都蒙在鼓里,好歹我也是一个主角啊,你知道叔叔去找我是怎么说的吗?他的借口是帮他剪羊毛。”她说:“他担心你很高傲,让你来相亲你不来。更何况对象是我这样的女人。”我说:“我要是知道来和你相亲,就会好好打扮一番,你看看我这个样子。不过我平时很干净,也经常洗澡,身上一点都不臭,不信你闻闻。”她说:“兰台吉,你这人真讨厌。”“我就是想说你的眼光很好,看中的男人很优秀。”“哼,谁看中你了?”“我说错了,是我看上你喜欢上你了。”我将车停住,扭过身子看着她说,“我还有一个问题,这好几年,你难道真不愿意再组建一个家庭吗?”她说:“一个带着孩子的老女人,谁会要呢?”我说:“看你这话说的,真不诚实。而且你还在讽刺我。”她说:“嗯?怎么会呢?”我说:“你这么漂亮年轻,又有好的气质,又能干,如果你还没人要,那我这样的男人又算什么?既没有长相也没有其他实力,我应该怎么评价自己?垃圾吗?”她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她表情有些僵硬地说,“哪有人这样作践自己的?”我说:“你也知道不能作践自己?难道你只会对自己提要求,而对别人宽容?”
她愣愣,捂嘴轻笑,眼神机敏地看着我。我们对视一眼,这下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她好像看穿了我所有的心思。
“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说的是有道理有依据的。男人越老越吃香,女人越老越悲惨,这不是人们嘴上的道理吗?再说,你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是想讥笑我?”我很郑重地说:“在这片草原上再没有比你更好的女人了。”她说:“我不善良,也不漂亮。”我接着说:“你说了不算,我觉得你漂亮善良就行了。”她问:“你是在表白还是在胡搅蛮缠?”我说:“我说了真心话,你却怀疑。如果我说一些真真假假的话,兴许你就信以为真了。所以这世界有时候真的是颠倒了看才正常。”“哎呀,说得好有道理,我都相信了。你再接着说。”她故意做出一副崇拜的样子。我问:“什么?你还想要,哎呀,你真是没个够。”[page]
我身上狠狠地挨了几拳。
我说:“对不起,我不该开这样的玩笑。”她说:“你这样说真的不对,更不应该。”我说:“我的心思都花在如何给你留下好印象上,而且我这个人也不够机灵,但我……”
她说:“是啊,你连脑子都不灵光了,却能说出这样的话,你根本就是故意的。”我说:“老天在上,我该怎么证明我的真心?”“你可以发誓呀。”她说。我发誓:“我一定会娶到我身边这个女人,无论上刀山下火海。”她语气平淡地说:“你真能说,像英格玛。”我说:“桑吉,如果你的美丽有一半是天生的,那么另一半就是你后天塑造的。你很了不起你知道吗?”“嗯,谢谢你。”她轻声细语地说。她还想说什么,但犹犹豫豫还是没说。
“你想了解什么,我都可以一五一十地告诉你。”我说。她说:“我不知道该不该问。”她看了我一眼,低下头,“你家里的事情我知道一些,但也是道听途说,我不知道……”
“我知道。但你看,我不是已经挺过来了吗?”我笑着说,“其实我不是放不下他们的死,车祸也是天灾,这是没办法的事,我认了。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会这样,不至于这样……”我知道脸上的泪水淌下来了,我不想这样,但我控制不住,这些话憋在心里这么久,我像抵挡魔鬼一样抵挡着,我怕我在人前崩溃,滔滔不绝地胡言乱语。我想问问,我就想问出声,为什么?
我收拾阿爸阿妈身体的时候,浑身的血液麻木了,我没有颤抖、没有逃避,我有那么一瞬间觉得他们在给我传递鼓励。那天,我一直没有怕。这些我不能跟她说。我擦了一把脸,吐了一口气,心颤颤的,我想我又放下了一片阴霾。是她将我从一种古怪的刻意的情绪中拉回来了。
她扶着我肩膀,泪水涟涟地说:“没事的,我们会好起来的……”
“是的。当然。感谢时间向前奔跑。”我握住她的手,接着往前开车。
6
我们到了叔叔家十分钟后,大雨猛地停歇,云层淡薄了。
桑吉进屋后稍坐片刻,便跟随婶婶到厨房准备午饭,两人小声咕哝,婶婶的笑声不时传出来。叔叔在家里待不住,刚刚进来喝一碗茶,套上雨靴又看牛去了。他们的宝贝孙子在炕上睡得香甜。
院子里积满了浑水。叔叔用红砖铺就的院子有两个出水口,但还有大量的雨水从大门流淌出去。我走到阳台,看着大沟的方向,我担心家里的情况,但我并不打算回去。我给我那朋友发了一条很长的微信,说了缘由。告诉他我还要三五天才能返回家中,请他务必多多费心。过一会儿,他回复:真正的缘分只有一次,遇到就别错过。等你凯旋,贺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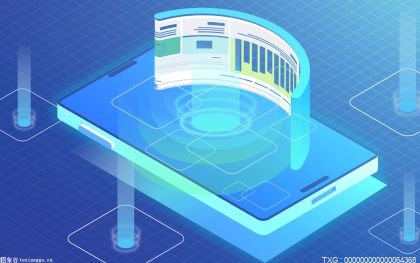


Copyright 2015-2022 上市公司网版权所有 备案号:京ICP备12018864号-25 联系邮箱:29 13 23 6 @qq.com